

恒常学习
孝为戒先 知恩报恩 佛门的孝亲观
在世俗大众的认识里,佛教往往被视作一方出离尘世、绝俗离伦的方外之教。然稽考经藏,方知佛教,一直将孝亲敬恩置于修行根本、善道枢要之地。

佛门之孝,既赅出世间之慧光,亦不离世间人伦之温情;其后东传中土,融汇传统儒孝,更凝练为东方文明中一道深邃而庄严的伦理奇观,非惟契理契机,亦且熠耀千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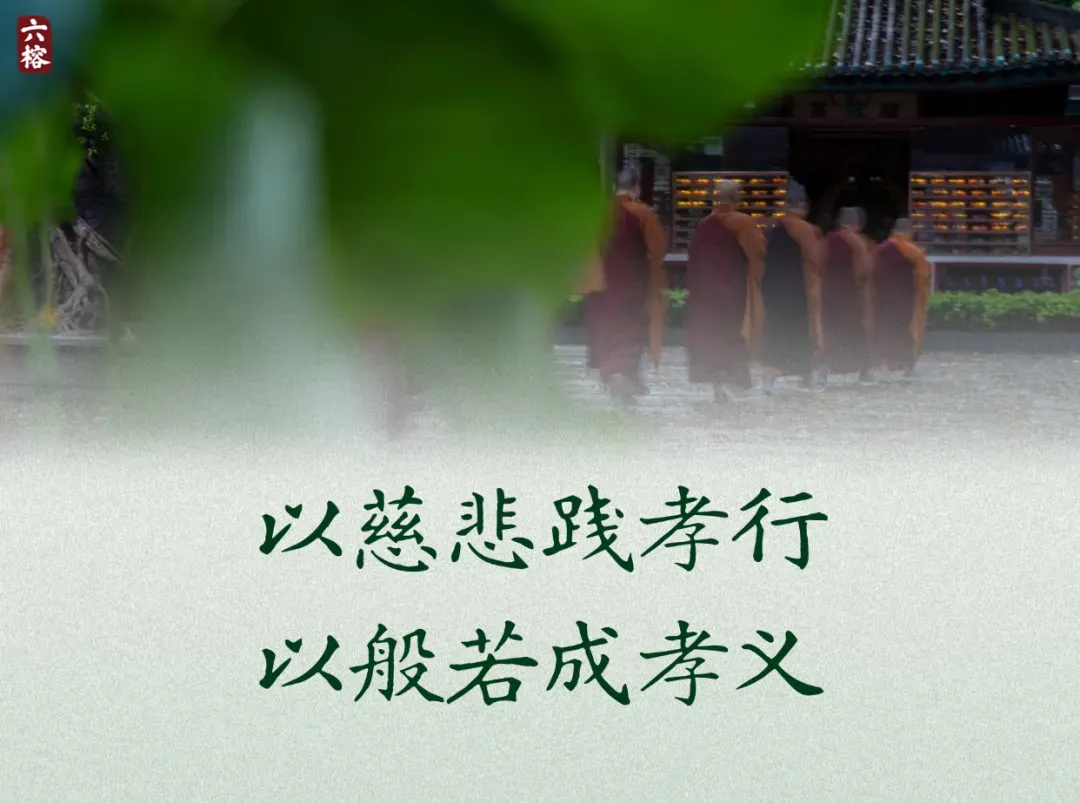
佛教经典素将孝道视为修行根本、善道之源。
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》中,殷重宣说:「父母恩深重,恩怜无歇时,起坐心相逐,近遥意与随。」经中佛陀更喻父母恩德如山高海深,纵然「左肩担父,右肩担母,研皮至骨,穿骨至髓」,亦难酬其恩。此经偈非仅是譬喻之辞,实乃基于缘起正观所阐述。一切众生,皆曾互为父母子女,故孝亲之本义,实为对轮回之中深重恩情的觉醒与体认。
《盂兰盆经》中所载的目犍连救母之事,尤见孝道与佛法救度之融合。目犍连尊者见母堕于饿鬼道中,悲怆不已,佛为说盂兰盆供之法,使七世父母皆得离苦。此经不仅确立孝亲之仪轨,更昭示大孝之深义。孝之要义,非止于世间奉养,更须以佛法智慧,济拔父母出于轮回。此种「出世之孝」,超越俗谛局限,彰显佛门孝道之特质,以慈悲践孝行,以般若成孝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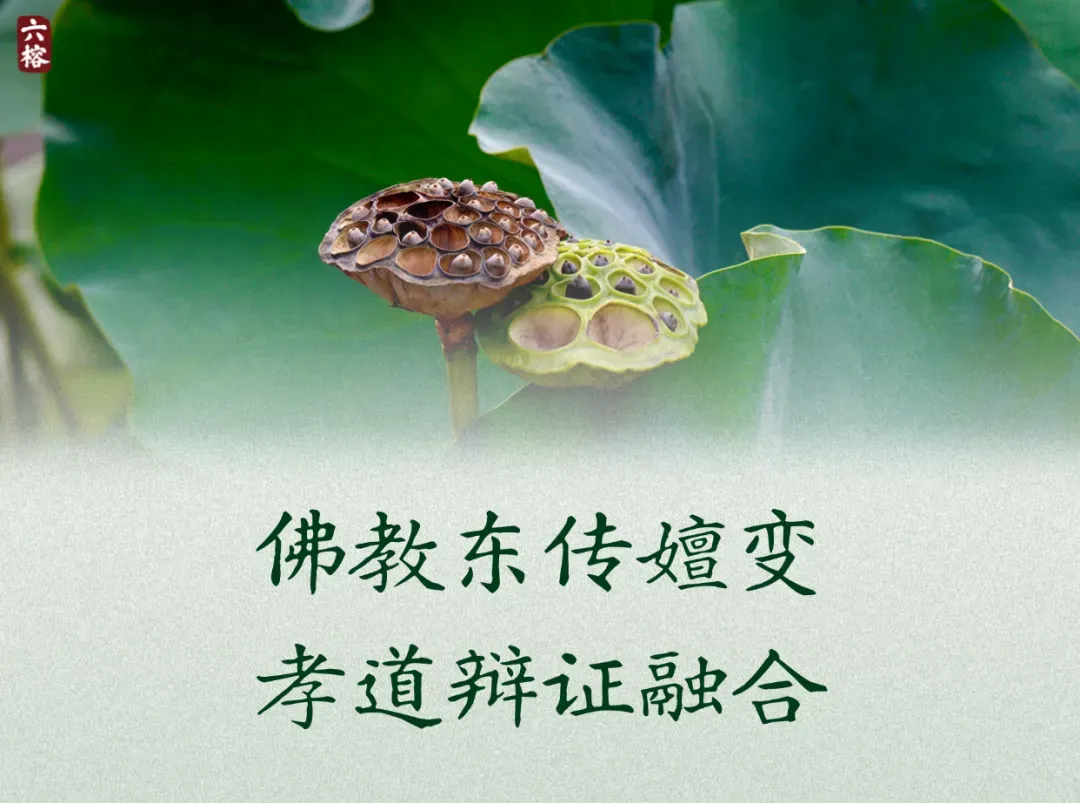
佛教初入中土时,曾因沙门剃发出家、不拜君王等制度,与中土固有的儒家孝亲伦理形成一定的差异冲突。
东晋高僧慧远和尚所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,对此进行了系统辨析。他指出,出家者「遁世以求其志,变俗以达其道」,其外在形仪虽异于世俗礼制,实则通过修道弘法、提升道德,以功德回报国家父母,乃至达成「大孝通于神明」的崇高境界。
至唐宋时期,佛教进一步与中土价值观融通,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孝亲观念。《六祖坛经》中,六祖惠能大师有偈云「恩则孝养父母,义则上下相怜」,将孝道纳入世间修行的体系中。
北宋契嵩禅师撰《孝论》十二篇,明确主张「夫孝,诸教皆尊之,而佛教殊尊也」,并以「孝为戒先」融通世孝与戒律,在理论层面实现了佛教伦理与儒家孝道的融合。这一融合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精神走向与社会认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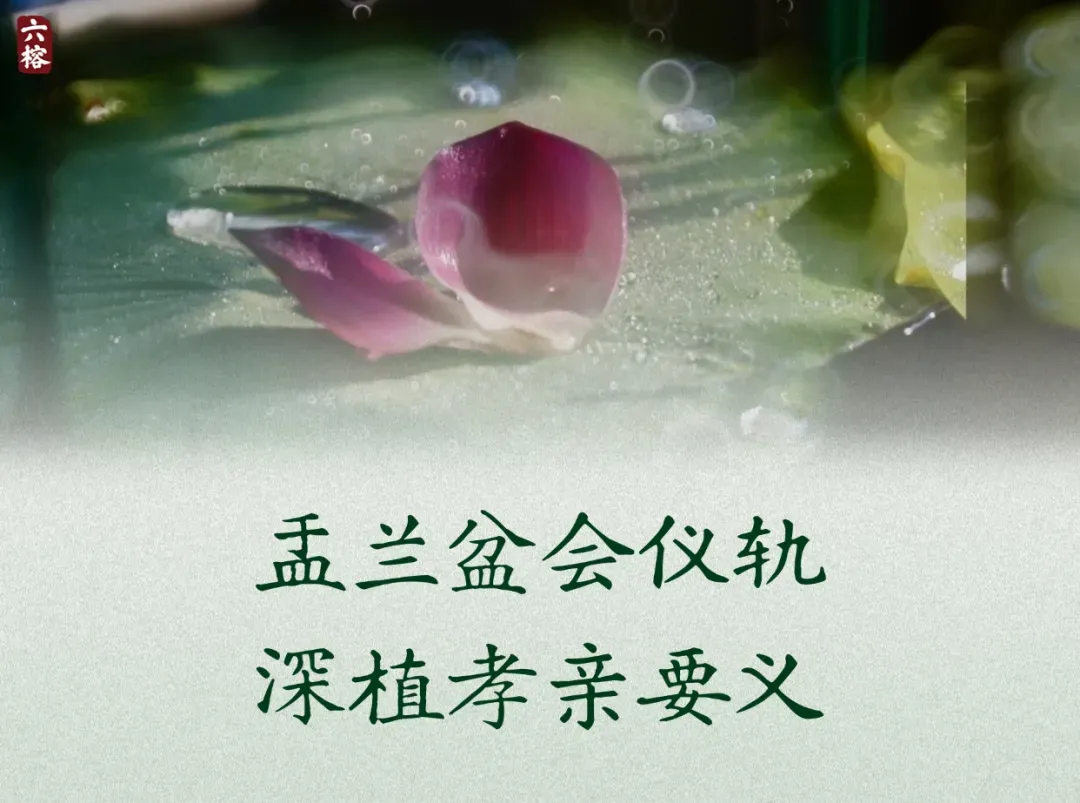
《梵网经》所阐述的「孝名为戒」,主张「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」,将世俗孝亲扩展为对一切众生的普遍慈悲。这一思想既与儒家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的推恩理念相契合,又以佛教轮回观为依据,奠定了实践仪轨的思想基础。
有了经文句偈作为依据,进而通过制度化的仪轨,将孝亲观念深刻融入宗教实践中,盂兰盆会的形成与发展便是其中的典范。
这一法会源于《佛说盂兰盆经》中目犍连救母的典故。自南北朝传入中土后,该经便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相结合。至唐代,宗密法师在《盂兰盆经疏》中强调孝道是「儒释皆宗之」的根本,贯通人伦与天道。他大力倡导在农历七月十五设盂兰盆供,以饮食供养十方僧众,藉此功德救度七世父母。这使得盂兰盆会迅速发展为融祭祀、超度与报恩于一体的孝亲法会,获得广泛社会响应。其后,清明、冬至等传统祭祖时节也渐成为僧俗共同践行孝道的重要场合。这不仅使盂兰盆节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,更体现出中国佛教对孝道文化的深刻融摄与升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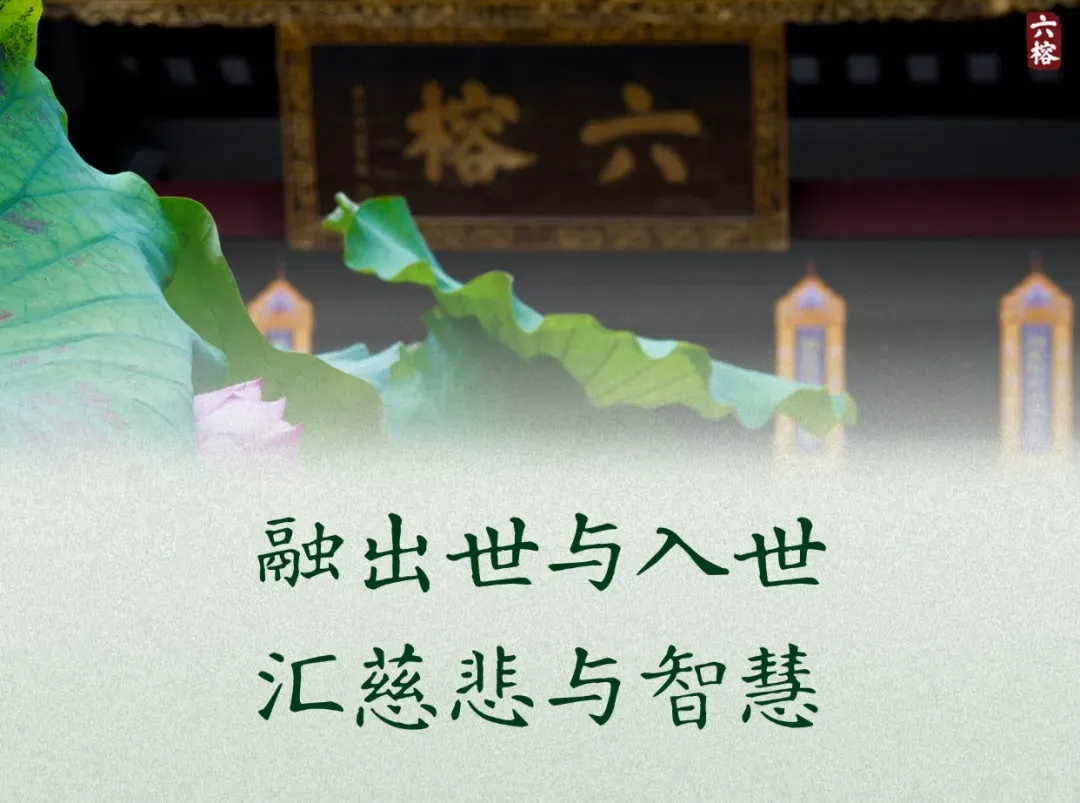
佛教孝亲观自印度至中国,历经创造性转化,既葆有解脱道之崇高愿力,亦实现与人伦日用的深切融合。其所启示者,乃真正之大孝,非惟晨昏定省、物质奉养,更在于以智慧引导父母出离轮回;非止于一世血亲之眷念,更是对一切众生皆曾为父母之深刻体认。
此一种融汇出世与入世、慈悲与智慧之孝亲观,恰如天台宗所云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」,于世俗伦理中彰明佛法真谛,于孝亲敬恩中践行菩萨精神。这既为佛门对中国文化之重大贡献,亦成为人类文明中一道超越时空的伦理光明,照亮现代人在个体修行与家庭责任、超越追求与人伦义务之间求得平衡的智慧之路。
图片及数据源:广州六榕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