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恒常學習
孝為戒先 知恩報恩 佛門的孝親觀
在世俗大眾的認識裏,佛教往往被視作一方出離塵世、絕俗離倫的方外之教。然稽考經藏,方知佛教,一直將孝親敬恩置於修行根本、善道樞要之地。

佛門之孝,既賅出世間之慧光,亦不離世間人倫之溫情;其後東傳中土,融匯傳統儒孝,更凝練為東方文明中一道深邃而莊嚴的倫理奇觀,非惟契理契機,亦且熠耀千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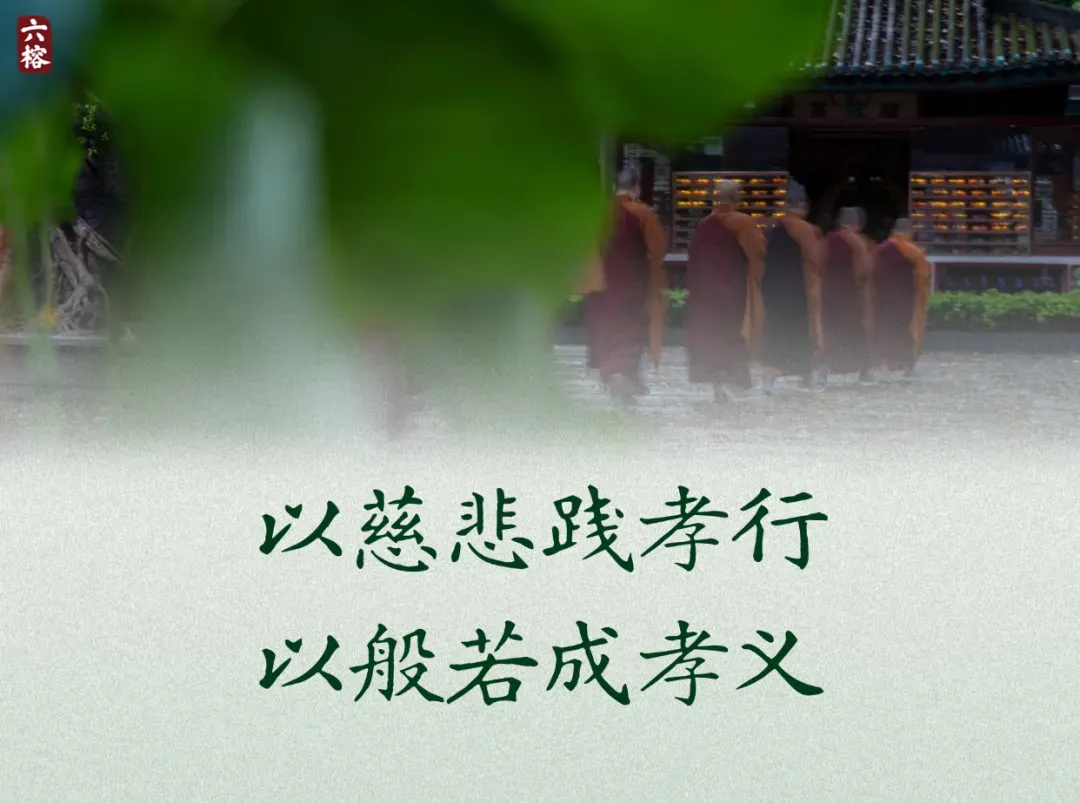
佛教經典素將孝道視為修行根本、善道之源。
《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》中,殷重宣說:「父母恩深重,恩憐無歇時,起坐心相逐,近遙意與隨。」經中佛陀更喻父母恩德如山高海深,縱然「左肩擔父,右肩擔母,研皮至骨,穿骨至髓」,亦難酬其恩。此經偈非僅是譬喻之辭,實乃基於緣起正觀所闡述。一切眾生,皆曾互為父母子女,故孝親之本義,實為對輪回之中深重恩情的覺醒與體認。
《盂蘭盆經》中所載的目犍連救母之事,尤見孝道與佛法救度之融合。目犍連尊者見母墮於餓鬼道中,悲愴不已,佛為說盂蘭盆供之法,使七世父母皆得離苦。此經不僅確立孝親之儀軌,更昭示大孝之深義。孝之要義,非止於世間奉養,更須以佛法智慧,濟拔父母出於輪回。此種「出世之孝」,超越俗諦局限,彰顯佛門孝道之特質,以慈悲踐孝行,以般若成孝義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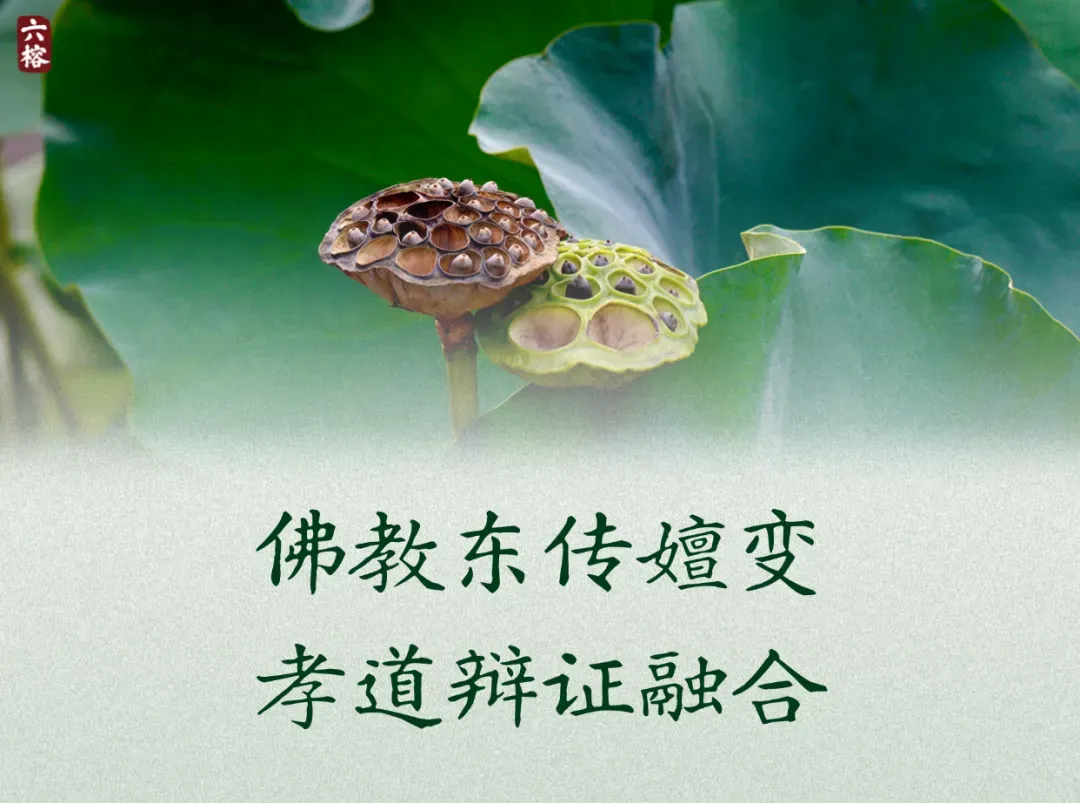
佛教初入中土時,曾因沙門剃髮出家、不拜君王等制度,與中土固有的儒家孝親倫理形成一定的差異衝突。
東晉高僧慧遠和尚所作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,對此進行了系統辨析。他指出,出家者「遁世以求其志,變俗以達其道」,其外在形儀雖異於世俗禮制,實則通過修道弘法、提升道德,以功德回報國家父母,乃至達成「大孝通於神明」的崇高境界。
至唐宋時期,佛教進一步與中土價值觀融通,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孝親觀念。《六祖壇經》中,六祖惠能大師有偈雲「恩則孝養父母,義則上下相憐」,將孝道納入世間修行的體系中。
北宋契嵩禪師撰《孝論》十二篇,明確主張「夫孝,諸教皆尊之,而佛教殊尊也」,並以「孝為戒先」融通世孝與戒律,在理論層面實現了佛教倫理與儒家孝道的融合。這一融合深刻影響了中國佛教的精神走向與社會認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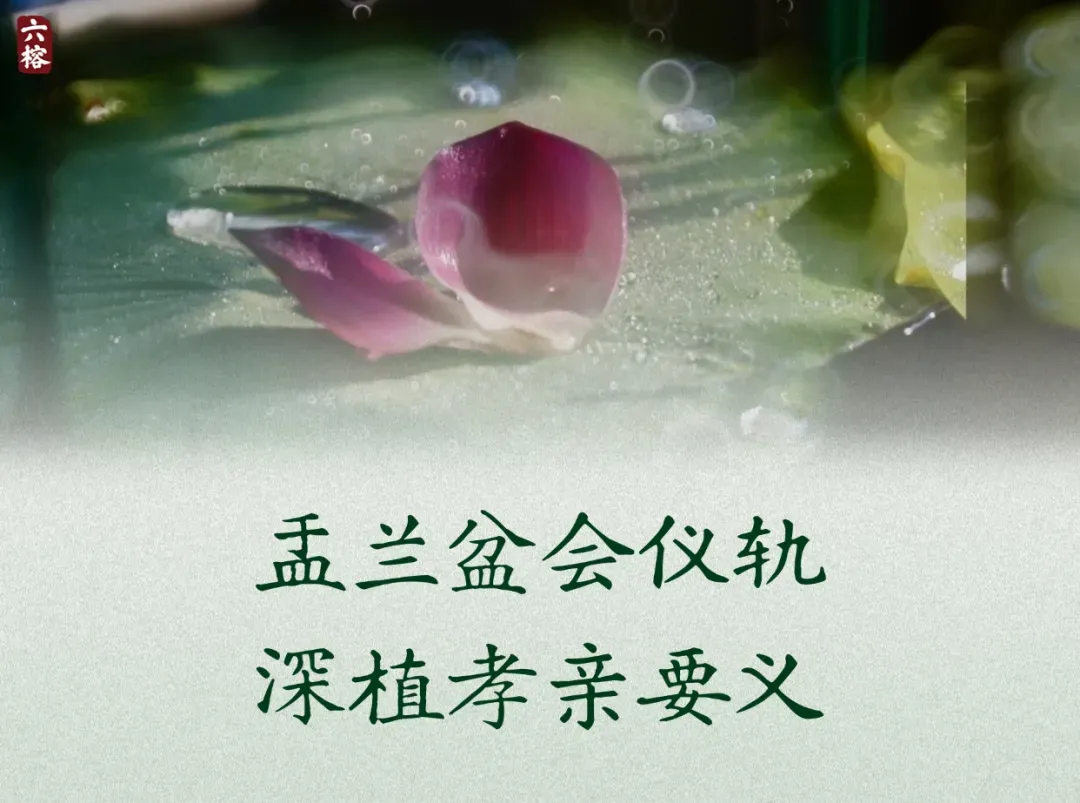
《梵網經》所闡述的「孝名為戒」,主張「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」,將世俗孝親擴展為對一切眾生的普遍慈悲。這一思想既與儒家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的推恩理念相契合,又以佛教輪回觀為依據,奠定了實踐儀軌的思想基礎。
有了經文句偈作為依據,進而通過制度化的儀軌,將孝親觀念深刻融入宗教實踐中,盂蘭盆會的形成與發展便是其中的典範。
這一法會源於《佛說盂蘭盆經》中目犍連救母的典故。自南北朝傳入中土後,該經便與中國傳統祭祀文化相結合。至唐代,宗密法師在《盂蘭盆經疏》中強調孝道是「儒釋皆宗之」的根本,貫通人倫與天道。他大力宣導在農曆七月十五設盂蘭盆供,以飲食供養十方僧眾,藉此功德救度七世父母。這使得盂蘭盆會迅速發展為融祭祀、超度與報恩於一體的孝親法會,獲得廣泛社會回應。其後,清明、冬至等傳統祭祖時節也漸成為僧俗共同踐行孝道的重要場合。這不僅使盂蘭盆節成為佛教中國化的典型代表,更體現出中國佛教對孝道文化的深刻融攝與昇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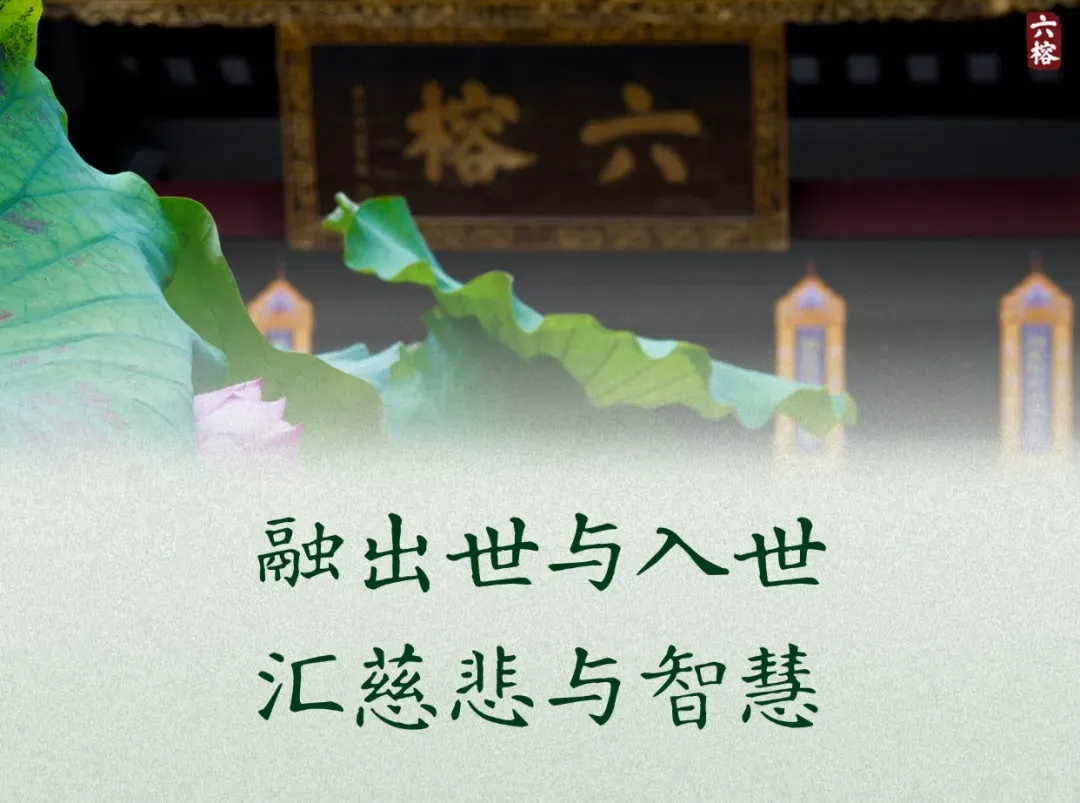
佛教孝親觀自印度至中國,歷經創造性轉化,既葆有解脫道之崇高願力,亦實現與人倫日用的深切融合。其所啟示者,乃真正之大孝,非惟晨昏定省、物質奉養,更在於以智慧引導父母出離輪回;非止於一世血親之眷念,更是對一切眾生皆曾為父母之深刻體認。
此一種融匯出世與入世、慈悲與智慧之孝親觀,恰如天臺宗所雲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」,於世俗倫理中彰明佛法真諦,於孝親敬恩中踐行菩薩精神。這既為佛門對中國文化之重大貢獻,亦成為人類文明中一道超越時空的倫理光明,照亮現代人在個體修行與家庭責任、超越追求與人倫義務之間求得平衡的智慧之路。
圖片及資料來源:廣州六榕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