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恒常学习

咒语念念有词
从某种意义上说,人是一种语言生命存在,这正如海德格尔说的:「事物要在言词中,在语言中才能生成并存在起来」。「唯当被表示物的词语已被发现之际,物才是一物。唯有这样物才是一物」。这就是说万物是借助于语言,才被指认出来的。

我们很多时都有这样的经验,若果没有人跟我们说话,就会觉得日子非常的难过。我们害怕孤独,当与人共处时,不习惯那沉默无言的场面,所以我们东拉西扯,胡乱地都会说一番说话,而很多时的话题,都离不开别人,这很容易就令自己堕入说三道四,是是非非的陷阱里。佛陀慈悲,知道语言的伤害性,了解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,所以告诫我们,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。说真实语、质直语,才可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互信。不两舌的意思是不要挑拨离间,应大事化小、小事化无,这个准则,在现在诉讼频密的社会特别适用。不恶口除了是不说污言秽语外,还包括不应对骂,要多说有建设性的说话,在这个谩骂文化充斥的世界,特别有警惕性。不绮语的意思是不要为了达到目的而花言巧语,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充满广告的世界,是有指导作用的。

在佛堂里,我们与师兄弟打招呼时,很多时都会说一句「阿弥陀佛」,其实这并不只是一句口头禅,因为所有佛的名号,都有其特别的意义,若能做到口到、耳到、心到,则可达到念念修行的目的。阿弥陀佛的名号,据鸠摩罗什译之《阿弥陀经》的记载,此佛光明无量、寿命无量,故称阿弥陀佛。梵本《阿弥陀经》及《称赞净土佛摄受经》则说,此佛寿命无数、妙光无边,故称无量寿佛、无量光佛。口诵佛号,是对自己和对方的祝愿,希望佛力加持自己和众生,所以可以达到修心的目的。若是修习净土法门的,更可以时常藉此提醒自己,学佛的目的和方向。有时我们又可以说「观世音菩萨」,这是慈心的修习,代表我们时刻都向观音菩萨学习,慈悲对待自己和众生,这就是为甚么我们中国佛教有句说话:「家家念弥陀,户户观世音」了。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很多时的说话都失实,甚至会无心犯错,多多利用这些时间念佛、念经、念咒,实不失为最有成本效益的修行方法。
作者:陈家宝医生

私人执业妇产科专科医生
于2011年取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(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)。
在港大修读时,曾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佛学会第一届主席。
数据源:香港普明佛学会

要想发财 别乱花钱
问:如何发财? 梦参老和尚答:「很简单,做布施」。梦参老和尚给大家讲个「竭尽施」的故事。佛在世的时候,有一个贫女很穷,讨口要饭,没有钱,她哪儿有钱?!忽然间捡了一枚金钱,这枚钱是金子做的。她捡了金钱,她就想了,为甚么我这么穷,人家那么有钱?因为我没有供养三宝,她说这回我可有了钱,我供养佛。

怎么供养呢?她到卖油的店里,就把这枚钱全买成油。这个店的油老板问她:「你要打油得拿个油具,不然你油搁到哪里?」 「我甚么都没有!」她说,「我这个钱是捡的,我因为穷我想供养佛。」老板也很感动,说:「好了,我给你拿个罐子,罐子是我的,油是你的。」
这个贫女把油就倒一个灯里头,还不是主灯,就倒了一个灯里头。她供养这一天,波斯匿王拉了十车油,把所有油灯都添满了,搁到那儿,也是都把灯添满点上了。贫女这个灯也不太大,但是光明特别大,比那个波斯匿王供的灯光明都大。
第二天早晨,灯要灭的时候,正好目犍连尊者当值,轮流着大家当班,目犍连尊者把别的灯都灭了,就是这个灯灭不了。在这个时间佛就出来了,说这个灯你罗汉的神通力量灭不了,说这叫竭尽施。甚么叫「竭尽施」?说她全部财产都供养灯了,那个贫女捐了她全部财产,全部供养。
完了佛就特别把这贫女找来,给她说法,她就证得阿罗汉果。就是一个灯,这叫「竭尽施」。
「舍得」即是「舍了才得」
布施的大和小,没有标准的。我说想发财,很多人想发财,一边要想发财,一边挥霍浪费。发了财,为了甚么?享受。
假使你发愿「发了财,供养众生」,那又不同了。要想发财,别乱花钱。
有一位台湾的朋友搞贸易,到了广东、上海,发了财,他不是忆念供养三宝,也不是再投入生产,有些大家可能听到的,到那儿去包二奶奶、包三奶奶都来了,他去享受了,这个发财不长久的。
为了众生发财,这是世间财。像大家都在这里「发财」,发甚么财呢?那叫「法财」。发财就得积福,不布施发不了财。「舍得」,我们大家都会说这句话,舍得舍得,你舍了才得,不舍不得。
数据源:内蒙古赤峰万佛寺

「四大皆空」是指那四个大呢?
不懂佛法的人,他会脱口而出地告诉你:「空了酒、色、财、气,就是四大皆空嘛!」其实,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,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。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,是指「地、水、火、风」的四大物质因素。

四大的观念,也不是佛教发明的,这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的结果,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,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。比如中国书经所记的「水、 火、金、木、土」五行;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的世界形成,是基于「地、水、风、火、空」的五种自然因素;希腊古哲学家恩比多克里斯 (Empedocles),也曾提出「气、水、土、火」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。
总之,不论五行也好,五大也好,四大也好,都是指的物理界的基本元素,如果仅限于此而胶着于此,那末,发展的结果,便是唯物论者,所以,这些思想,也是唯物论的先驱。
佛教讲四大皆空,是沿用着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刻化及佛教化的,因为地、水、火、风的四大元素,是宇宙物理的,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,海洋河川属于水 大,阳光炎热属于火大,空间气流属于风大。如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,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,血液分泌属于水大,体温属于火大,呼吸属于风大;若从四大的物 性上说,坚硬属于地大,湿润属于水大,温暖属于火大,流动属于风大。但是,不论如何地分析四大,四大终属于物质界而无法概括精神界的。所以唯物论者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,佛教则绝不同意这样的说法。

佛教所讲的四大,也有小乘与大乘的不同。从大体上说,小乘佛教所说的四大,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,称为四大种,意思是说,地、水、火、风,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,一切的物象,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;四大和谐,便会欣欣向荣,四大矛盾,便会归于毁灭,物理现象是如此,生理现象也是如此, 所以佛教徒把病人生病,称为「四大违和」。小乘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,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,不以色身为实在的我,不因执取色身为我而造种种生死之业,一旦把我看空,便会进入小乘的涅盘境界,不再轮回生死了。
大乘佛教所说的四大,不是指的根本元素,而是指的物态的现象,是假非实,是幻非实,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,仅是增上缘而非根本法,虽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 种子,但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;小乘佛教因为只空我而不空法,所以虽把物象看空,仍以为四大的极微质--「法」是实有的。不过,小乘佛教不是唯物论,而是多元论,因为佛教的空不仅空去四大,乃要空去五蕴;四大,祇是五蕴中的一蕴而已。
甚么又叫做五蘊呢?
那就是: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,前一属于物质界,后四属于精神界,四大,便是色蕴。
关于五蕴的内容,已非本文所能介绍,因为五蕴是个很大的题目,我们只能在此说一句:五蕴是三界之内的生死法,空去五蕴,才能超出三界的生死之外。同 时,我们由于五蕴的提出,证明佛教不是只讲四大皆空,而是要进一步讲五蕴皆空的。尤其重要的,佛教的重心,并不以四大为主,而是以识蕴为主,至于受、想、 行的三蕴,也是识蕴的陪衬,乃是用来显示精神界的功用之广而且大的。所以,佛教不仅不是唯物论者,倒是唯识论者。
数据源:香港佛教联合会

善用其心:设大施会 示如实道
手执锡杖、当愿众生、设大施会、示如实道。从这首偈颂开始,即是菩萨在乞食道行时所发大愿,共有五十五愿,分为三部分:一、十二愿,游涉道路时愿;二、十九愿,所睹事境时愿;三、二十四愿,所遇人物时愿。

锡杖,音译为隙弃罗、吃弃罗。又作声杖、有声杖、智杖、德杖、鸣杖、金锡。略称杖。比丘十八物之一。即比丘行于道路时,应当携带之道具。原用于驱赶毒蛇、害虫等,或乞食之时,振动锡杖,使人远闻即知。
《锡杖经》中说:「是锡杖者,名为智杖,亦名德杖。彰显圣智,故名智杖;行功德本,故曰德杖。」《华严经疏》中说:「锡者,轻也,明也。执此杖者,轻烦恼故,明佛法故。」
大施会,即无遮大会。无遮,宽容而无遮现之谓。不分贤圣、道俗、贵贱、上下,平等行财施及法施之法会,称为无遮会。
这句偈颂是说,当菩萨准备去乞食,拿起锡杖之时,即发愿一切众生,皆能设大施会,广行布施,并以此开显真如实相之道。
善用其心
〈净行品〉是八十卷《华严经》的第十一品,此品请法主智首菩萨向文殊师利菩萨提问:作为菩萨,如何清净身、口、意三业,自利利他,成就佛道,共一百一十个问题。
文殊菩萨则以「善用其心」一法,总答智首菩萨的提问,指出若能在生活善用己心,身、语、意三业都会清净,又分别提出了一百四十一条愿行,指导凡夫念念不离众生,把握当下随事发愿。
心为一切法之本源,用于善,则善,用于恶,则恶。让我们一切学习实践菩萨清净愿行,触事留心,随时发愿,善用己心,早成佛道。
图片及数据源:杭州灵隐寺

身如客舍 心似旅人
「人生如逆旅,我亦是行人。」人生是一场艰难的旅程,几经波折而不休,你我都是天地间的过客。人生如寄,我们要把身体当作自己的客人一样,照顾好它而又不执着于它。

调适身心
修行就是要把习气、毛病改正过来。我们要善加调适自己的身心,饮食要节制,不要暴饮暴食;作息要规律,不要拼命地熬夜,拼命加班;有适当的运动,不要让愚痴、烦恼障碍了自己的身心;要以智慧对待自己,以慈悲对待众生,以平稳的心精进修行。
「身心要松,工夫要紧。」这才是真精进,对于我们的修行以及健康也才有所帮助。
「非暴力」地使用自己的身体不仅是修习正念的一种方式,它本身就是一种修习。
破除我执
我们一般人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最重要的,所以就把自性忘了。其实这个身体,并不是真「我」,只是「我的」身体。佛陀教导我们,身体里并无固定不变的我,但我们却执着它为自己,认为它就是我。
「身如客舍,心似旅人。」要知道,这个身体它只是「我」暂时住的一个房子。当我们把身体看作是一位客人、一个房子,就会明白人生就像是旅客寄宿一般,只是短暂地停留,不必生出太执着的心。
我们读诵「色无常、受无常、想无常、行无常、识无常」,并非为了增加愚痴,而是为帮助与了解身体的实相,好让我们可以放下,并舍弃执着。
我们这个色身是虚妄的、是无常的;但是我们为了护持正法的缘故,我们还是应当要爱惜自己的身命,何况它还是我们修行的道器。所以我们在精勤精进的时候,还是要善加调适身心,用智慧去觉察,修到内心自然生法喜。
数据源:广州光孝寺

咒語
咒语,在一般人心目中,是充满神秘性和神性的口语,但从语言的角度而言,咒语的语言是通俗化的,一般人都可以念诵,其纯朴、简洁与童谣无异。咒语的流行,在中国有其长远的历史,以巫山为中心的巴蜀地区,就是张道陵创立道教最早的流派“五斗米教”的发源地。

荆楚地区,在春秋战国时就形成了重鬼尚巫的习惯,在《楚辞》中就有许多巫术降神的记载。历代的统治者,对巫术、仙术亦深信不疑,好像汉武帝、秦始皇等一代天娇,都迷信于方士的长生不老药,而在隋唐宋三朝,更把符咒治病手法列入太医十三医中的一种,称为「祝由科」将那些术士封为「咒禁博士」,这说明了官方对符咒治病的肯定态度。在历史中,用咒术治病而见效,很多时是因为施咒的巫师,具有一定的医术,既是巫师,又是医师。在现代的中国,很多气功师都有传授咒音,这里面以藏密的咒音居多,但也有一些道家功法修持中的咒音,但却缺乏科学或医学上的文献来支持其疗效。
咒语,在佛教中又作神咒、禁咒、密咒、真言或陀罗尼,是指不能以言语说明的特殊灵力之秘密语。印度古吠陀中即有咒术。依长阿含经卷十四载,释尊曾驳斥咒术,然杂阿含经卷九载,释尊曾说毒蛇护身咒,故知咒术于甚早时即普遍于印度,且为佛教所采用。大乘教派之般若、法华、宝积、大集、金光明、楞伽等显教经典,均有载录咒文之陀罗尼品;密教则更加重视密咒,认为咒即「法尔常然」之表示,若诵读观想,即能获得成佛等之利益。活跃于我国佛教入传初期之外国僧侣,长于咒术者颇多,如北凉昙无谶被誉为西域之大咒师,即其一例。

咒原作祝,是向神明祷告,令怨敌遭受灾祸,或欲袪除厄难、祈求利益时所诵念之密语,故此咒语有善咒、恶咒之别。善咒,如为人治病,或用于护身之咒;恶咒,如咒诅他人,使之遭受灾害之咒。法华经卷七普门品、旧华严经卷五十七、十地经卷四等,皆有述及此类恶现语句;药师如来本愿经等,即言必须远离此等恶咒。使用恶咒之恶鬼有毘陀罗(起尸鬼)等。世尊禁止弟子修习咒术、以咒术谋生,仅允许以咒治病或护身。经典中所述之咒极多,如长阿含卷十三阿摩昼经、卷十四梵动经等之水火咒、安宅符咒、剎利咒等;四分律卷二十七、十诵律卷四十六等之治腹内虫病咒、世俗降伏外道咒等;生经卷二护诸比丘咒经之蛊道符咒等。中国佛教流行的咒语,有十小咒、大悲心陀罗尼、楞严咒和心经等。念诵咒语,是修心的法门,心调则身调,若正确理解持咒的力量,不偏重神通变化,不与传统医学对抗,对治疗心身病是应有其一定的效用的。
 作者:陈家宝医生
作者:陈家宝医生
私人执业妇产科专科医生
于2011年取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(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)。
在港大修读时,曾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佛学会第一届主席。
数据源:香港普明佛学会

立定「弘法利生」之愿
证严上人思想体系中的立定「弘法利生」之愿。荣华富贵如浮云,在无常的人世间,何必为了无常的情爱,而将个人限制在一个家庭中。为什么一个女人只为了一个家庭,提菜篮子就满足了,为什么范围这么小?那时我想到很多人遇到困难时,都会叫「观音妈、妈祖婆」,他们也是现女人身,却能因应众生需要而随处显现。

我感觉应该要立志。对普天下的众生,我们都可以用妈妈的心去爱,如果被一个家庭拘束了,又能爱多少人呢!所以,应该要去小爱,成就大爱。虽然当时我年龄还轻,不过,很向往这条路,自己也很笃定应该怎么走。
后来曾经有一段时间,我因身体不适,暂居于慈云寺静养,见及师父们为赶赴经忏,即使夜半时分亦得整装外出,当时我虽尚未立定「弘法利生」之愿,但内心产生了疑惑,认为出家是神圣之事,真正的修行生活不应如此,深感应提升佛法教育,以道理开启人心。首要之务,应破除当时民间对佛教的迷信做法与观感;再者,佛法应运用于自身,落实于生活,而修行人则要提升生活的品格。
于是萌生寻找出家目标的念头,寻思将来若出家,如果不能兼利天下,就要独善其身。这是我「发心」之始…
图片及数据源:慈济环保全球信息网

安住于死亡 临终与丧葬
有关如来存在的真实样态之讨论,无论声闻乘或大乘都展示出佛陀与一般人迥乎不同的理解,而这与如来入灭后的样态为何之问题,紧密相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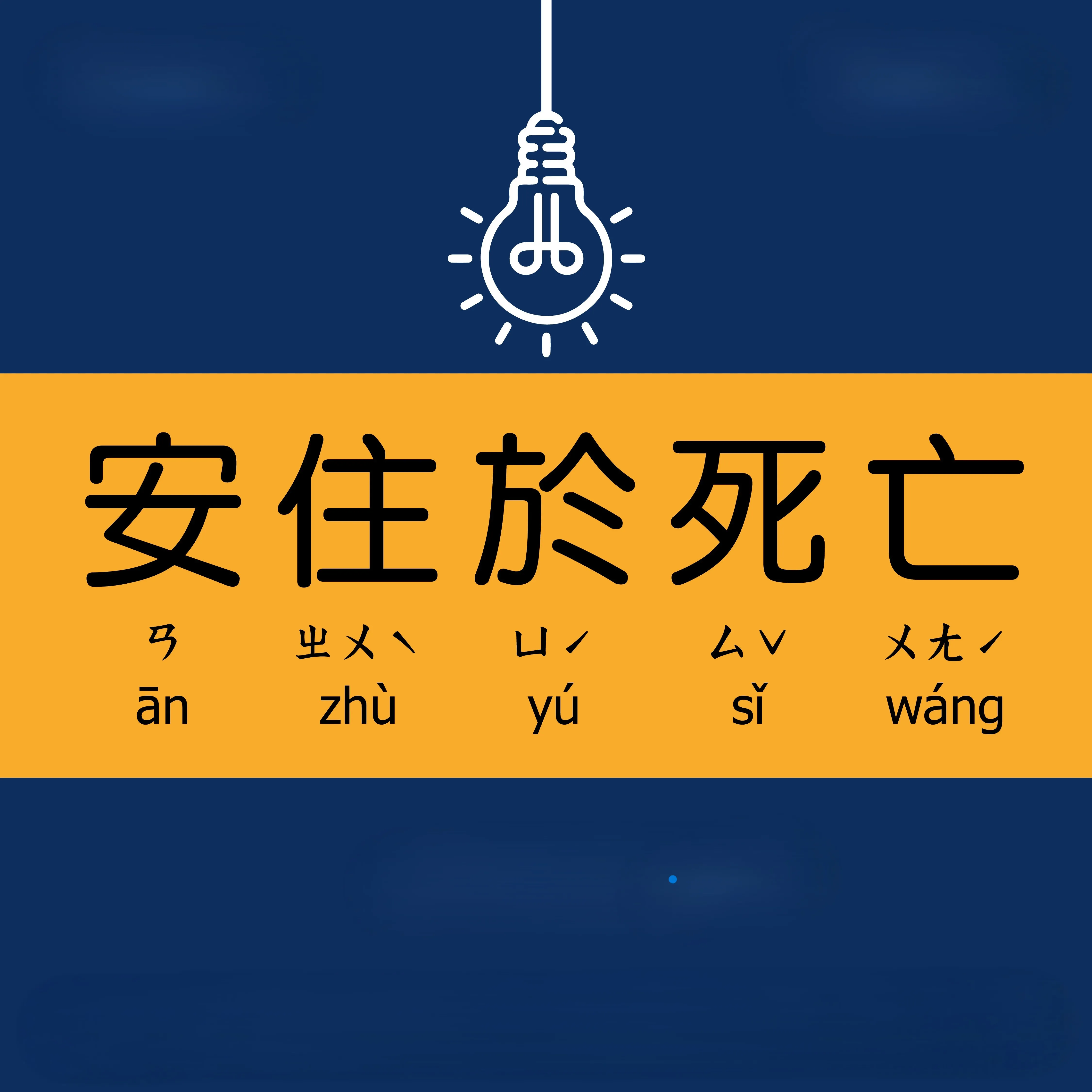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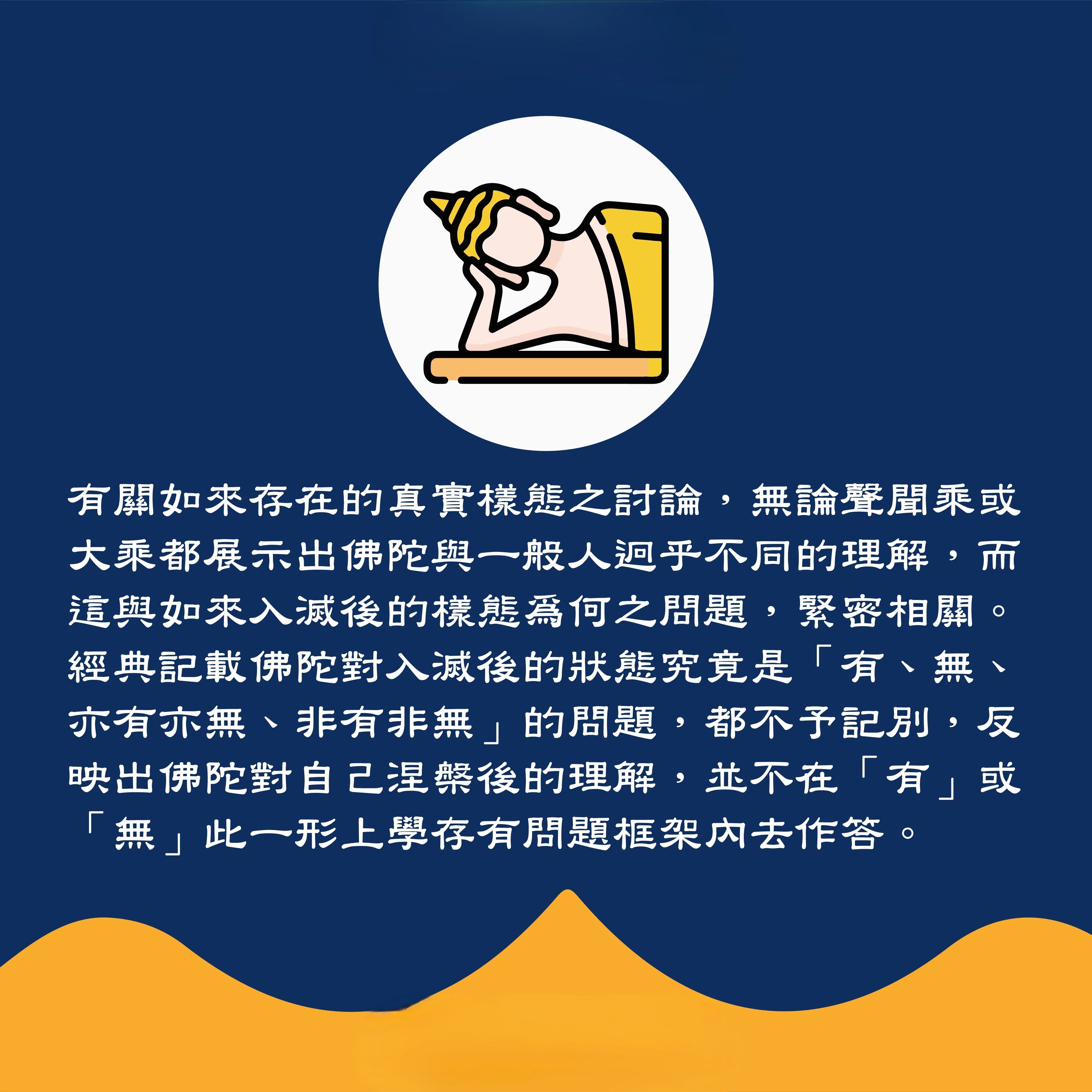
经典记载佛陀对入灭后的状态究竟是「有、无、亦有亦无、非有非无」的问题,都不予记别,反映出佛陀对自己涅盘后的理解,并不在「有」或「无」此一形上学存有问题框架内去作答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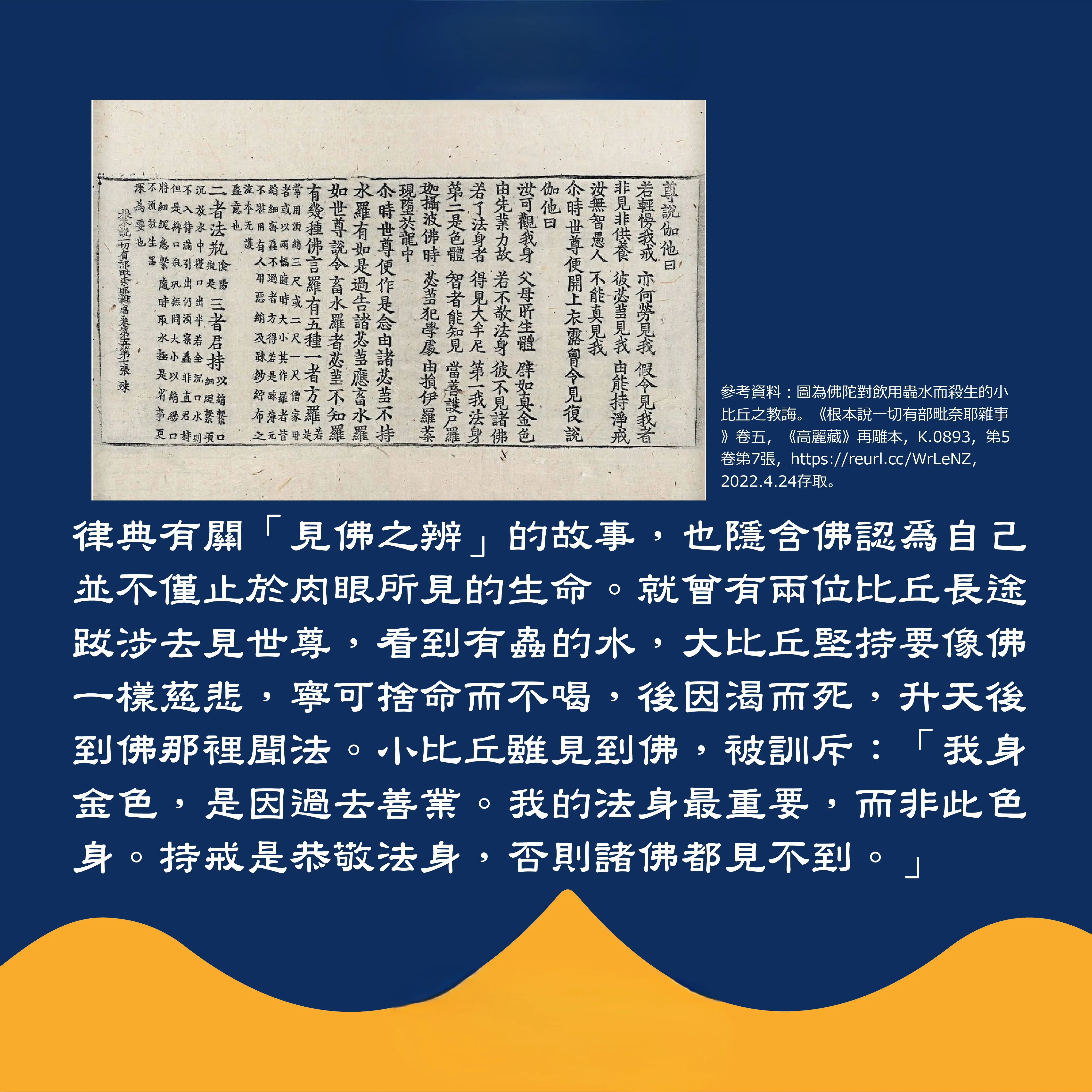
律典有关「见佛之辨」的故事,也隐含佛认为自己并不仅止于肉眼所见的生命。就曾有两位比丘长途跋涉去见世尊,看到有虫的水,大比丘坚持要像佛一样慈悲,宁可舍命而不喝,后因渴而死,升天后到佛那里闻法。小比丘虽见到佛,被训斥:「我身金色,是因过去善业。我的法身最重要,我的法身最重要,而非此色身。持戒是恭敬法身,否则诸佛都见不到。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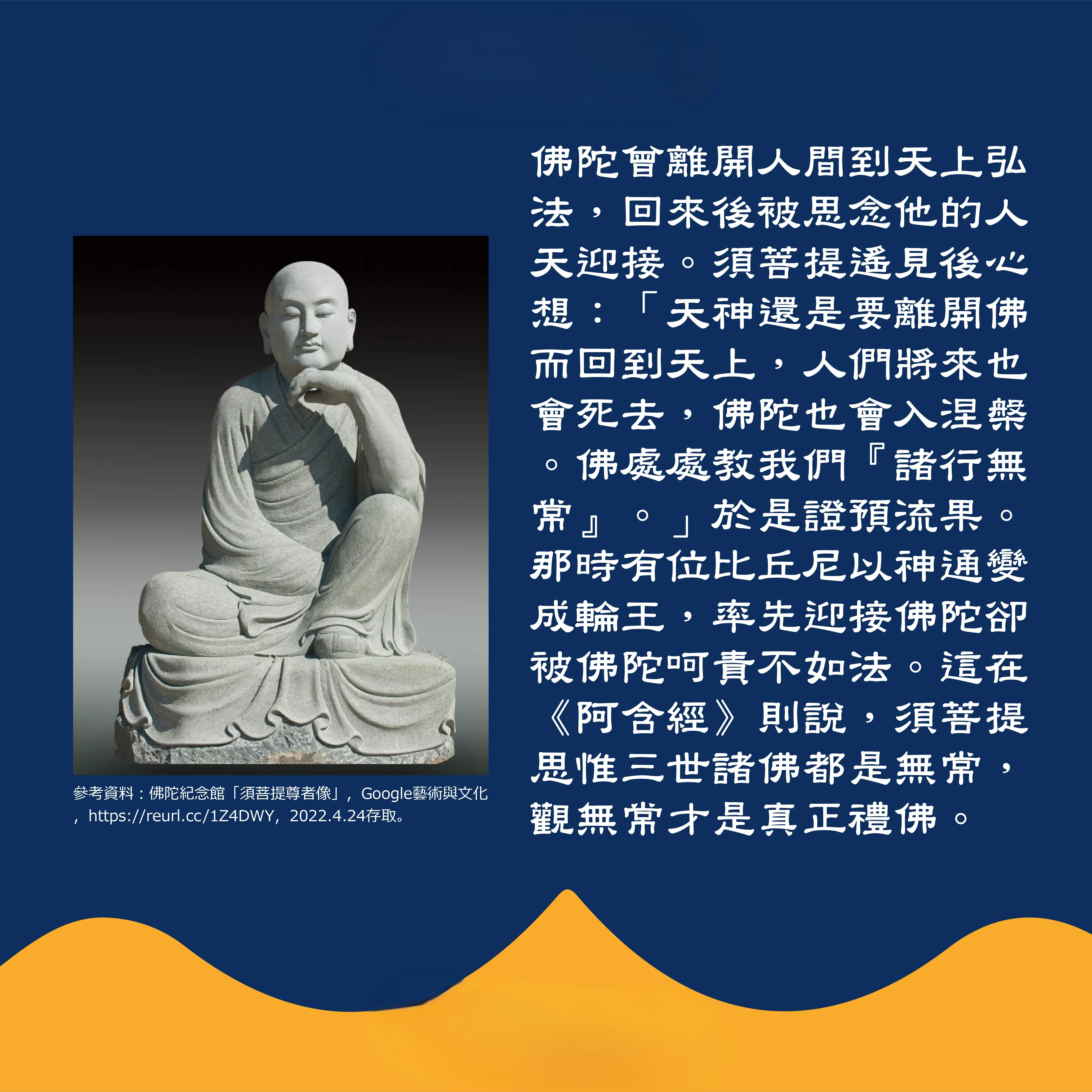
佛陀曾离开人间到天上弘法,回来后被思念他的人天迎接。须菩提遥见后心想:「天神还是要离开佛而回到天上,人们将来也会死去,佛陀也会入涅盘。佛处处教我们『诸行无常』。」于是证预流果。那时有位比丘尼以神通变成轮王,率先迎接佛陀却被佛陀呵责不如法。这在《阿含经》则说,须菩提思惟三世诸佛都是无常,观无常才是真正礼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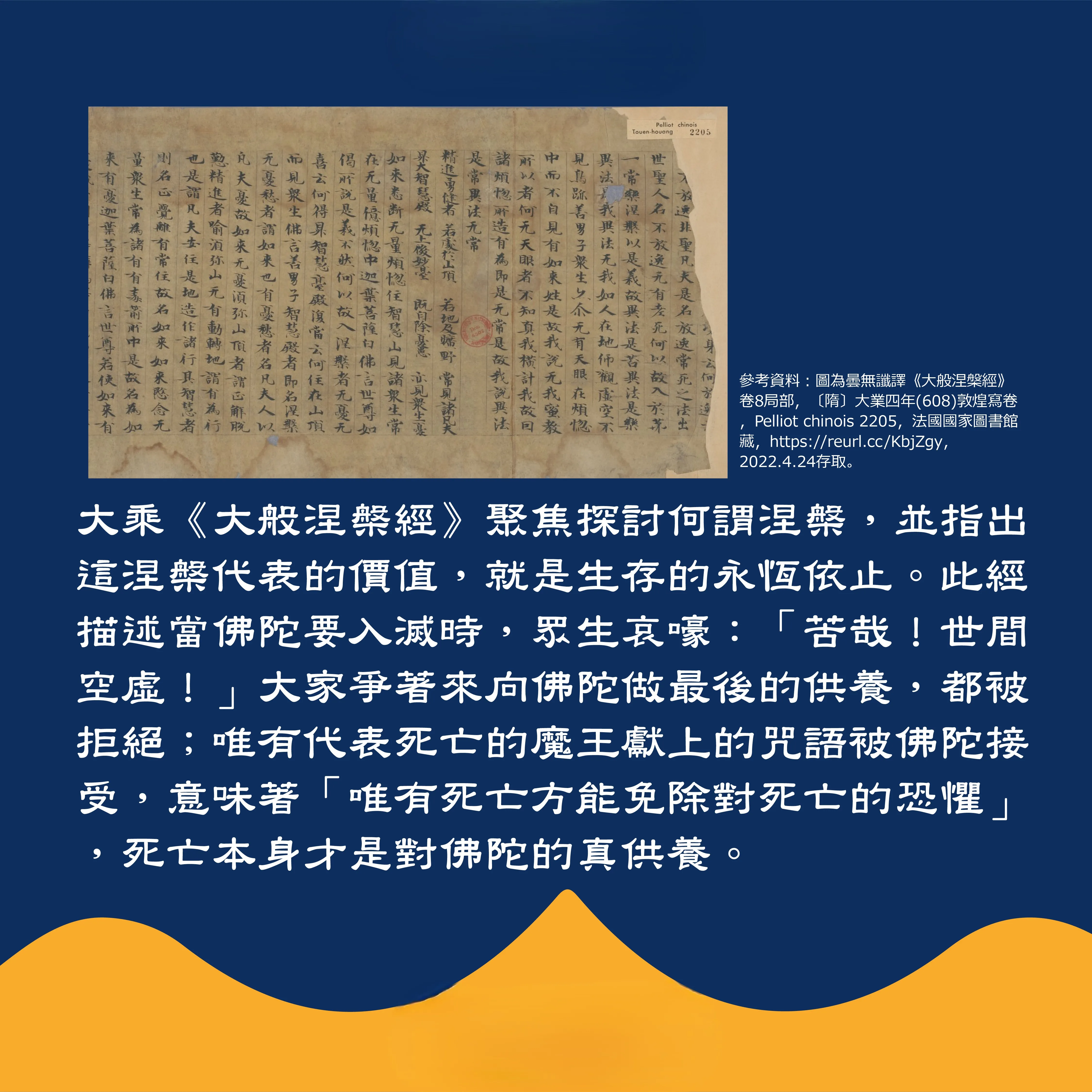
大乘《大般涅盘经》聚焦探讨何谓涅盘,并指出这涅盘代表的价值,就是生存的永恒依止。
此经描述当佛陀要入灭时,众生哀嚎:「苦哉!世间空虚!」大家争着来向佛陀做最后的供养,都被拒绝;唯有代表死亡的魔王献上的咒语被佛陀接受,意味着「唯有死亡方能免除对死亡的恐惧」,死亡本身才是对佛陀的真供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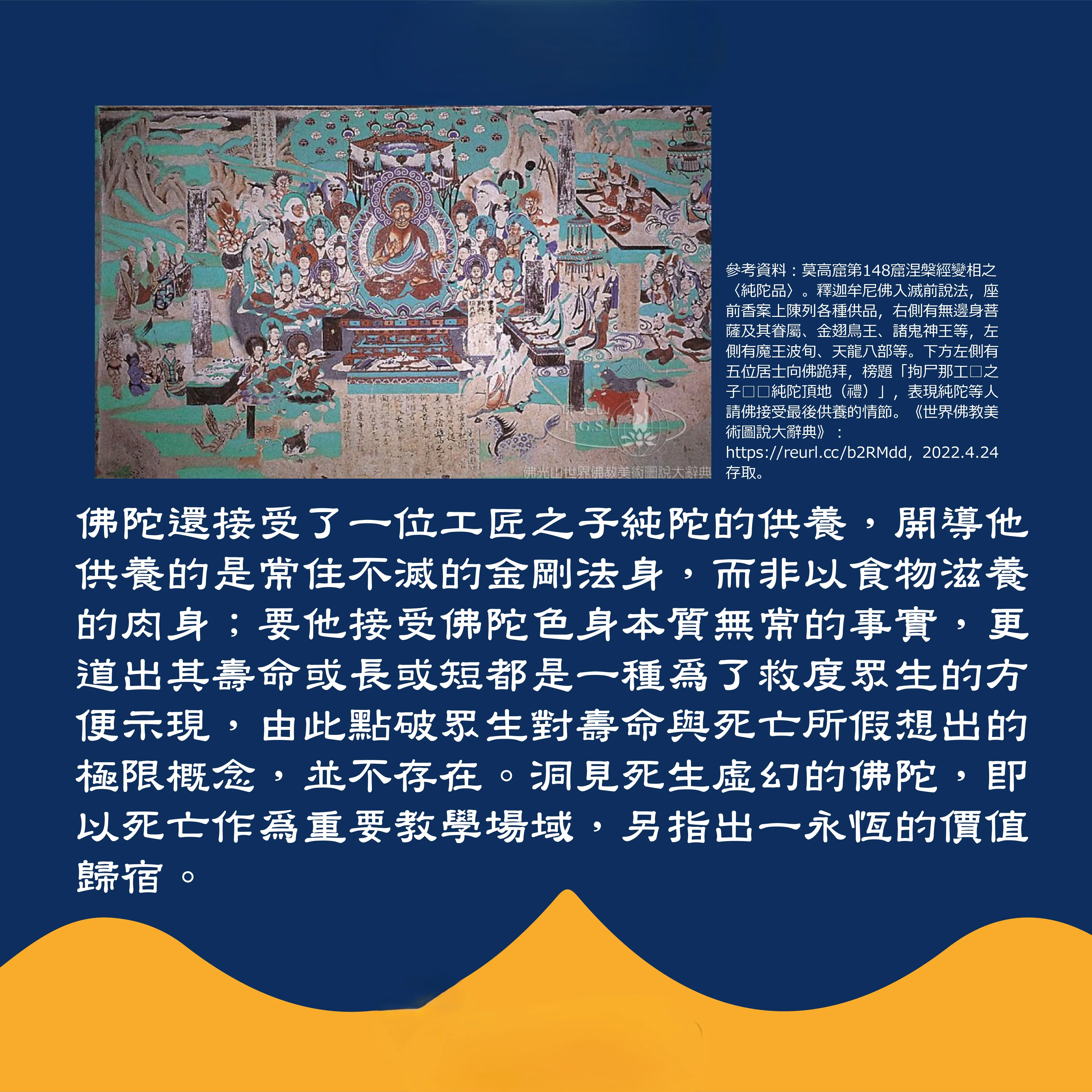
佛陀还接受了一位工匠之子纯陀的供养,开导他供养的是常住不灭的金刚法身,而非以食物滋养的肉身;要他接受佛陀色身本质无常的事实,更道出其寿命或长或短都是一种为了救度众生的方便示现,由此点破众生对寿命与死亡所假想出的极限概念,并不存在。洞见死生虚幻的佛陀,即以死亡作为重要教学场域,另指出一永恒的价值归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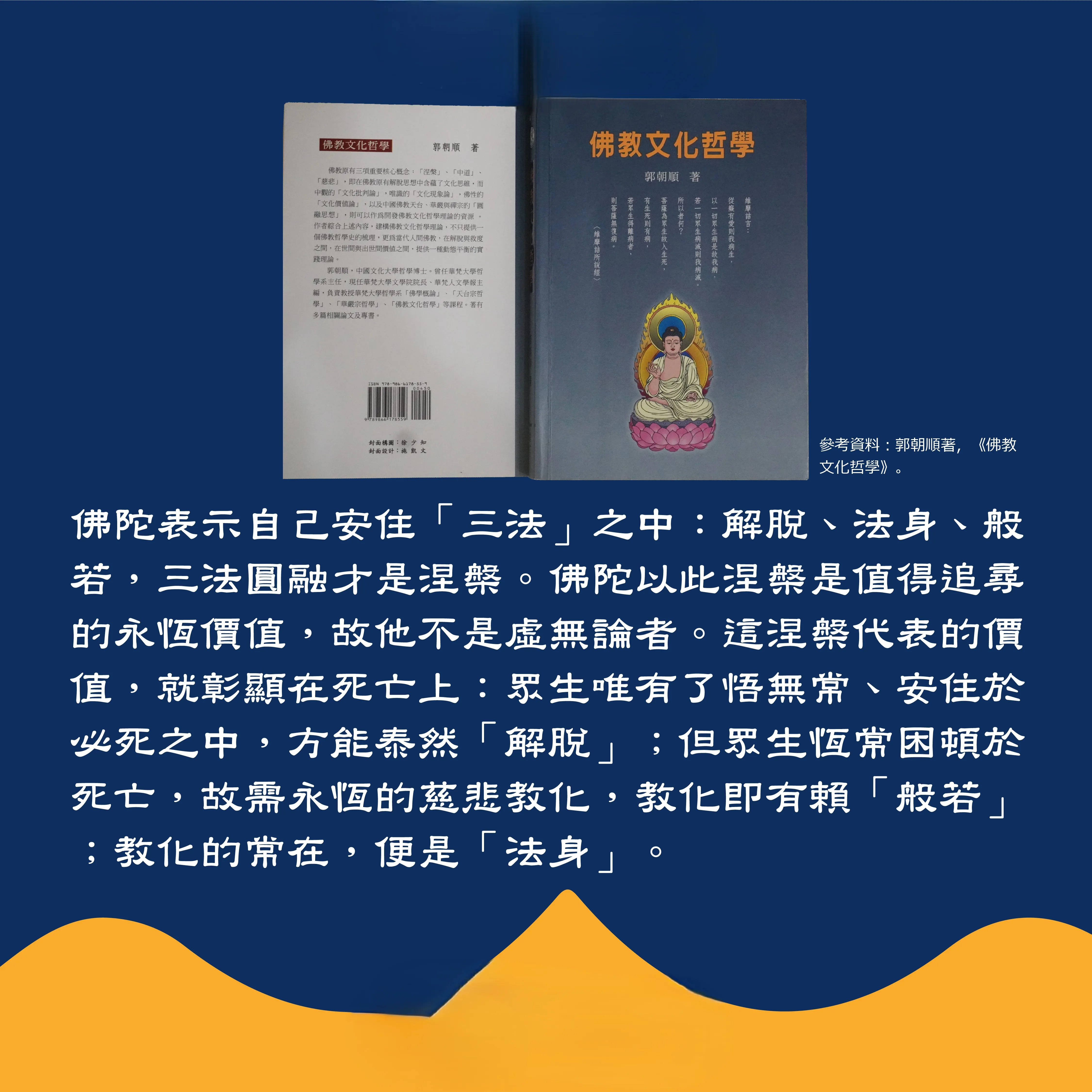
佛陀表示自己安住「三法」之中:解脱、法身、般若,三法圆融才是涅盘。佛陀以此涅盘是值得追寻的永恒价值,故他不是虚无论者。这涅盘代表的价值,就彰显在死亡上:众生唯有了悟无常、安住于必死之中,方能泰然「解脱」;但众生恒常困顿于死亡,故需永恒的慈悲教化,教化即有赖「般若」;教化的常在,便是「法身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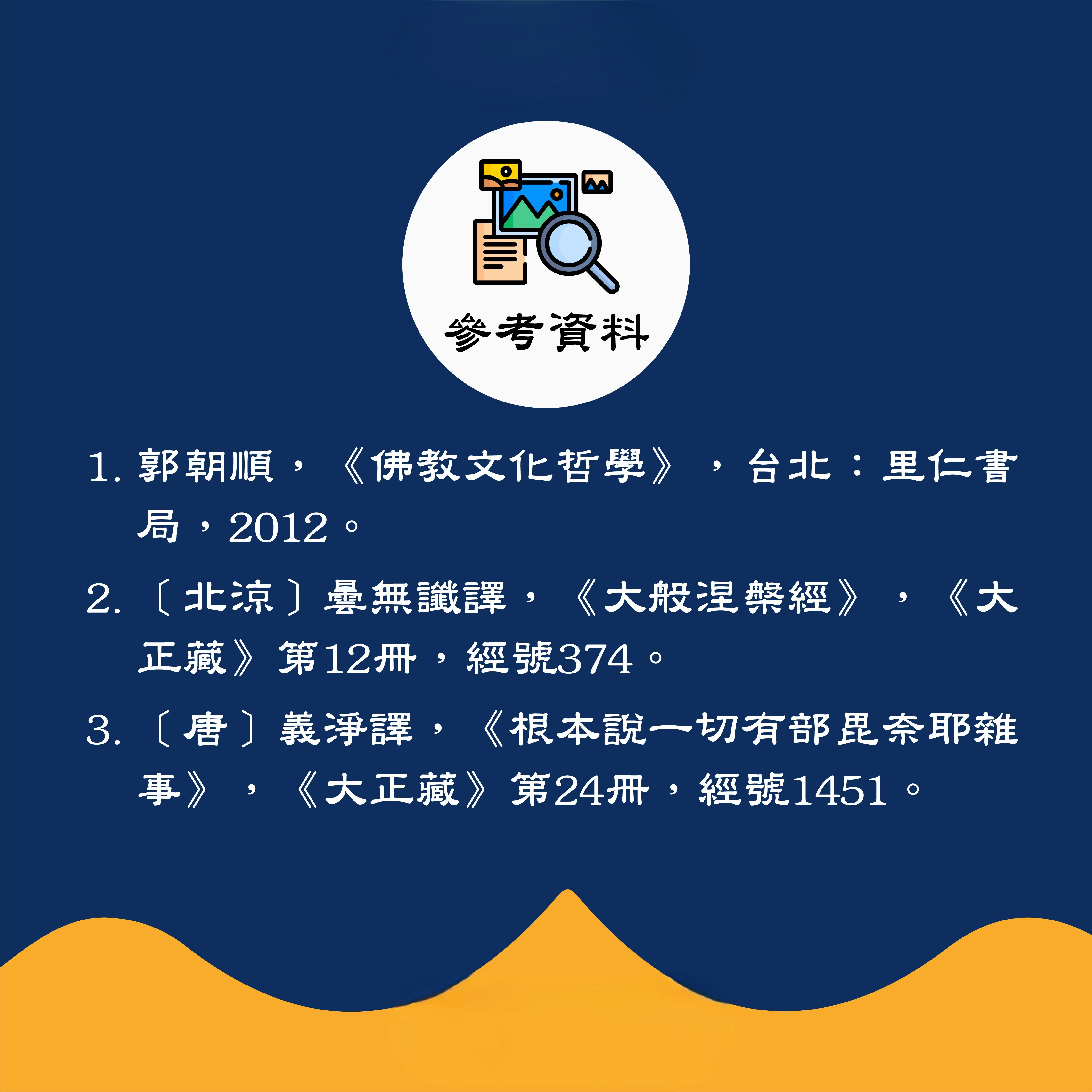
参考数据1:郭朝顺,《佛教文化哲学》,台北:里仁书局,2012。
参考数据2:〔北凉〕昙无谶译,《大般涅盘经》,《大正藏》第12册,经号374
参考数据3:〔唐〕义净译,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》,《大正藏》第24册,经号1451。
作者: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博士生 释知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