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恒常學習

如幻觀 | 止惡生善隨緣度
「隨緣」二字,我們于日常生活中時常聽到。可究竟甚麼是「隨緣」呢?也會有人慣將「隨緣」解釋成「躺平」和「隨便」,事實果真如此嗎?若想隨緣,就要認識緣;要是不能認識緣,我們所說的隨緣,只不過是戲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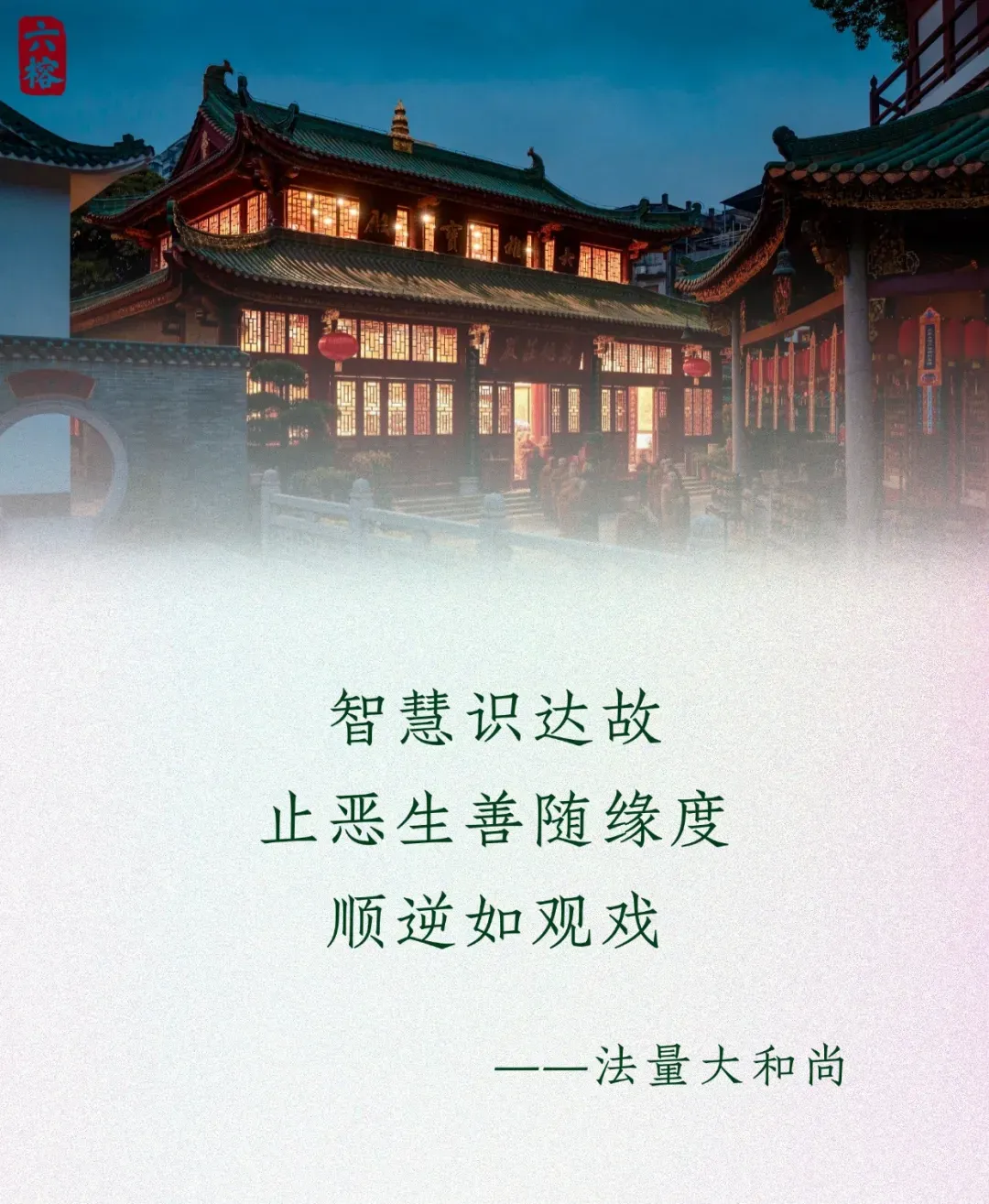
佛法上的「緣」,是因緣果報,有因有緣方有果。「單因不立,獨緣難成,因緣和合,方能生法」。
「因緣和合,方能生法。」
好比我們耕種田地,種子是因,其他促成種子成長的條件,包括土壤、陽光、雨露等就是緣,而所結成的果實就是果。只有種子,或是只有其他種種外在條件,都不能結果,這就是「因緣和合,方能生法。」
認識了「緣」是一切法皆依因緣而生起,自然也就知道「隨緣」是隨順因緣,而不是隨便,不是無所謂,不是躺平,不是糊裡糊塗,不是愛咋咋地,而是在因上努力做正確的事,在果上知足無求,坦然對待。
但也要明白,隨緣,是隨順善緣,而不是隨順惡緣。要修學讓苦止息、讓樂生起的因緣,要不斷地累積廣大的善法因緣,不斷地止息一切不善法的因緣,就像四正勤一樣——已生惡令斷滅,未生惡令不生,已生善令增長,未生善令生起。

法量大和尚說:「隨緣並非隨心所欲地放縱,也不是任性妄為地行事,更不是消極地聽天由命或空想等待。隨緣是生命覺醒後的智慧體現,是對因果深信不疑的洞達之境。它意味著能夠明辨善惡並做出正確抉擇,是恥惡欣善的勤勉勇敢之舉,更是有著但問耕耘、不問收穫的泰然心境。
當我們真正理解隨緣的內涵時,便不會在生活中盲目行動或消極等待。隨緣的智慧讓我們在面對各種境遇時,既能保持內心的平靜,又能積極地做出努力。
深信因果使我們明白每一個行為都有其後果,從而更加謹慎地做出選擇。明辨善惡讓我們堅守道德底線,朝著美好的方向前行。恥惡欣善則激勵我們不斷努力,摒棄不良行為,追求善良與美好。而但問耕耘、不問收穫的泰然,讓我們專注於過程,不被結果所束縛,以更加從容的心態面對生活的起伏。」

如同法量大和尚的一首漢俳所言:「智慧識達故,止惡生善隨緣度,順逆如觀戲。」隨緣,從來都不是被動消極,不是不思進取,而是正觀緣起,智慧抉擇。
在人際關係上,接納自他不同,不強求改變對方;在事業目標上,全力以赴,但不過分焦慮成敗;面對逆境違緣時,將困難視為修行的契機,而非抱怨命運……在現實生活工作中,努力斷一切惡、修一切善,了知一切皆是依因待緣所生,唯求自利利他之行,無住生心,知足感恩,謙和包容,恭讓慈愛,祝福一切。
正如大和尚開示所言:「知足感恩是人生幸福的源頭活水,是照見緣起表像的智慧結晶,它消融苦難如春日化雪,轉化逆境若秋月盈虛。智者馭心端行,勤勉向上,馴伏驕奢如馴烈馬,淬煉苦寒若臘梅幽香,在禍福流轉間識得方向,遇逆不餒,逢順不湎,始終以澄明之心照見緣生緣滅,使生命之舟乘風破浪駛向幸福的彼岸。」
圖片及資料來源:廣州六榕寺

別再苦上加苦
佛法中所說的苦有兩種,身苦和心苦。老病死屬於身苦,是色身的自然規律,即使聖者也會存在。 精進修學的佛弟子能看清,色身是五蘊和合的「假我」,就不會為之左右。當然這並不是完全不管,而是該治療就治療,該調養要調養,但沒有怨忿、抗拒、煩惱的情緒。同時,良好的心態有助於恢復健康,即使無法根治疾病,至少也能改善自己與照顧者的生活狀態。

除了疾病,在工作、情感、人際等各方面遭遇的挫折也都是這樣,看清萬事都是因緣和合而來的,因緣不具足則散,本質上就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,也從來沒有「事事皆如我心意」的人生。身已經苦了,只能及時止損,別再苦上加苦,白挨這第二支毒箭,再讓自己心苦了。
圖片及資料來源:上海玉佛禪寺

身苦心不苦
一次,佛陀住在摩揭陀國王舍城郊外的一處山中,被飛來的碎石片刺傷腳部,並且流血。但佛陀心中保持正知正念,默默承受身體的痛苦,心中卻不起煩惱。還有一次,佛陀遊化到恒河下游北岸的跋耆國,住在設首婆羅山一處有野鹿出沒的林中。某日,來了位120歲的老居士那拘羅,他向佛陀頂禮問訊後說:「世尊!我年紀大了,常常為衰弱與多病的身體所苦,行動很吃力,每次來見世尊與幾位我敬重的善知識比丘,都很不容易。但願世尊為我說法,讓我長久獲益,永遠安樂。」

佛陀說,「善哉!正如你所說的,上了年紀的人,身體必然多病痛,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你應當這樣學,我的身體雖然病了,但是我的心不病。」那拘羅聽後覺得很歡喜,禮謝佛陀後就離開了。隨後,那拘羅愉快地去見正在不遠處樹下打坐的舍利弗尊者,舍利弗明顯看出那拘羅容光煥發、精神愉悅。「剛剛世尊以甘露法灌溉滋潤我的身心呢!」 那拘羅轉述了佛陀的開示。
舍利弗問,「你何不繼續問佛陀,甚麼情況是心隨著身體生病而生病?甚麼情況是心不隨著身體生病而生病?」那拘羅知道舍利弗智慧第一,轉而請求舍利弗詳加解說。於是,舍利弗說道:不曾聽聞正法的愚癡凡夫,對自己色身的生起、消失、味著、禍患、出離(苦、集、滅、道、味、患、離「七處善」)不能如實了知,就會對色身產生了貪愛執著,以致於以為這是生命主體的「我」,要不,就以色身是「我」所有的而執著於它。所以,當色身發生變化敗壞了,心就隨之而動,生起憂、悲、惱、苦、恐怖、顧念、不舍、障礙了。

同樣的道理,對自己的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也一樣,一旦以為其中哪一個是生命主體的「我」,或者為「我」所擁有,或者在「我」之中,或者其中有「我」,只要以為生命中有一個不變的「我」是生命的主體,其結果就必然是——色身有苦時,心也跟著苦。甚麼情況下,心不會隨著身體生病而生病?多聽聞正法的佛弟子,對色身的生起、消失等都已如實了知,與之前所說的愚癡凡夫相反,對色身不會貪愛樂著……不認為有生命不變的主體的「我」並產生執著,那麼當色身發生變化敗壞時,心不會隨之牽動,就不會有憂、悲、惱、苦、恐怖、顧念、不舍、障礙了。
聽完舍利弗的解說,那拘羅老居士有了深徹的理解與體悟,當下證得法眼淨:見法、得法、知法、入法,不再需要靠別人而能解決自己的疑惑,于正法中,心不再畏懼。他從座位上站起來,整理好衣服,恭敬地合掌,對舍利弗說:「大德!我已經證悟,得到超越與度脫。現在,我歸依佛、法、僧眾,為佛弟子,請當我的見證人。從現在起,我終身歸依三寶。」
資料來源: 上海玉佛禪寺

何解梵唄是一種心靈環保 讓人心轉染為淨呢?
黃昏時分,寺院裡的鐘磬相和,僧眾隨木魚與引磬的節律唱誦經偈,這便是梵唄。所謂梵唄,是佛教的唱誦之聲,用清淨平穩的旋律持誦佛號、經文、偈頌與陀羅尼,常見於早晚課、法會與齋儀。它不是舞台表演,而是法事中的修行之道,以聲攝心,令散亂歸於安定。古德稱「梵」為清淨與梵音之義,「唄」即讚頌之歌,合而為能淨心的法音。

為什麼說梵唄是一種心靈環保?環保是減少污染、恢復清澈;梵唄則是減少心的污染,讓本具清明顯現。唱誦時,身體端正,呼吸放長,語、身、意三者同向,讓煩躁與妄念像渾水靜置,自會澄清。《法句經》言:「諸惡莫作,眾善奉行,自淨其意,是諸佛教。」自淨其意,不只是觀念轉念,而是透過可操作的工夫讓心逐步清淨,梵唄正提供了這樣的載體。
它如何轉染為淨?第一是聽覺的回向內觀。《楞嚴經》觀音法門揭示:「反聞聞自性,性成無上道。」人容易被外境的聲音牽引,梵唄把聲源穩定在佛號與偈頌上,讓我們順著聲波回聽自心,注意力從外散轉為內定。第二是呼吸與節律的調服。整齊的節拍令氣息均勻,心率平穩,心便不易躁動。第三是語義的導向。所唱的是覺悟、慈悲、願力之詞,文字像路標,帶動情緒與價值取向向善。《佛說阿彌陀經》說: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,聞說阿彌陀佛,執持名號,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、若四日、若五日、若六日、若七日,一心不亂。」名號是最簡約而有力的內容,反覆持誦,使心專一。
心耳「聽」出內在的聲線
不少初學者怕自己聲音不好,其實梵唄重在調心,不在炫技。可以從最簡單的佛號或短偈開始,聲量以自己能聽見又不費力便可,讓一句一息自然相隨。在不便出聲的環境,亦可默念,以心耳「聽」出內在的聲線。當環境嘈雜時,不用對抗噪音,只需把注意力重新放回那條穩定的旋律,久之便能在動中見靜。《維摩詰所說經》說:「若菩薩欲得淨土,當淨其心。隨其心淨,則佛土淨。」環境未必即刻改變,但心淨之處,自有清涼。
從這個角度看,梵唄確是心靈的環保,它減少情緒與語言的「廢氣」,回收散亂的注意力,讓心的「可再生能源」定與慧一一被啟動。當我們以梵唄攝心,染著因習漸輕,清淨與慈悲自然生起。等到聲息止時,那份安然仍在,像雨過天青,水本來就清,只是塵垢暫時被拂去而已。
參考文章
1.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(鳩摩羅什譯),CBETA
2. 《大佛頂首楞嚴經》卷六(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),CBETA
3. 《維摩詰所說經·佛國品》(鳩摩羅什譯),CBETA
4. 《法句經》偈183,CBETA
作者:甯瓏
香港中文大學佛學研究碩士畢業生。
緣份,就像種子要遇見陽光和水才能成長。每一種偶遇或許都不是巧合。既然我們有緣相聚、相識、相處或求學,就不必執著這是因,還是果,只要活好自己每一刻,真誠對己對人,必是有智慧的人。

身苦時 心就別再跟著受苦了
在釋迦牟尼佛涅盤後,當時的佛弟子們為了將佛陀的教法結集起來,召集了五百阿羅漢,由阿難尊者根據昔日聽聞的佛陀教法,當眾複述誦出形成了《阿含經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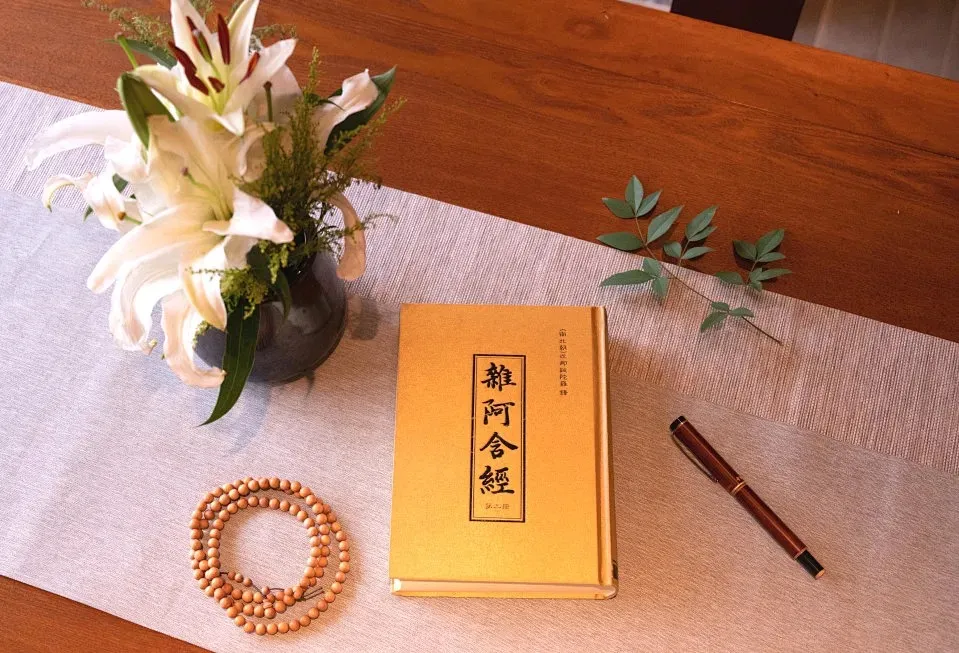
《阿含經》裡有不少故事和譬喻,都是佛陀對於弟子和比丘們的修行問題所做的回答和點撥,以及與修行相關的譬喻故事,相對容易理解。當年比丘們在修行中出現的問題或偏差,或許也正困擾著如今的佛弟子們,有些故事的對話似乎正映射著現今出現的一些現象。以下選取阿含經中的故事,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示。
第二支毒箭
一次,佛陀在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北郊的迦蘭陀竹園,問比丘們:「一般人都有樂、苦或不苦不樂的感受,有修有證的佛弟子也有這些感受,但和一般人有些甚麼明顯的差別呢?」比丘們答不上來,請求佛陀為大家解說。

佛陀開示道,一般人遇到生理上的各種苦痛,甚至於有致命之虞時,心裡禁不住地生起悲傷憂愁、痛苦怨歎,繼而憤怒迷亂而失去理智。這時,有「身受」與「心受」這兩種感受交相增長蔓延。就像有人中了一支毒箭,接者馬上又中第二支,成了苦上加苦的雙重痛苦。
這是因為一般人的無知,讓他們在歡樂時就縱情享樂,成了欲貪煩惱的奴隸不自知;痛苦時生氣不悅,成了瞋患煩惱的奴隸而不自知;在不苦不樂時,則渾沌不明,對於苦、樂兩種感受的生成原因、消失變化、餘味黏著、終是禍患、必須捨離等,都沒有真切如實的證知,成了愚癡煩惱的奴隸而不自知。這樣,當他快樂時,就被快樂所牽絆;痛苦時,就被痛苦所牽絆;連不苦不樂時,也被不苦不樂牽絆著,這就是深陷「貪瞋癡」,為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所牽絆的一般人。
但是,有修有證的聖弟子就不一樣了,當他們遇到生理上的各種苦痛,甚至於有致命之虞時,心裡不起悲傷憂愁、不痛苦怨歎、不憤怒迷亂,所以不會失去理智。這時,他只有一種感受,那就是「身受」,而沒有「心受」。就像中了一支毒箭後,不再中第二支。
當他們有樂的感受時,心不染著,所以不會成為欲貪煩惱的奴隸;有苦受時心不染著,所以不會成為瞋患煩惱的奴隸;在不苦不樂時,對苦、樂兩種感受的成因、消失變化等有真切如實的證知,不會成為愚癡煩惱的奴隸。這樣,就不會被樂、苦或不苦不樂所牽絆,解脫了貪嗔癡的控制。
資料來源:上海玉佛禪寺

佛陀出家和修行給我們的啟示
年青的佛陀文武雙全,他的生活雖然美滿幸福,但卻為了找不到人生的真理和生活的意義而煩惱。他覺察到傳統文化(婆羅門教)不能解決人類所面對的痛苦(生老病死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憎怨會),便下定決心找出原因和解決的方法,於29歲出家《普曜經.卷四》。

在恒河流域行腳六年,參訪了許多大師,即所謂六師外道(見於《佛說梵網六十二見經》),研習他們的道理和方法,修習禪定,最後嚴修苦行六年,但這一切都不能使他得到解脫,最終在尼連禪河邊佛陀伽耶(在今比哈爾邦內伽耶地方)的一棵菩提樹下靜坐,夜睹明星,見一顆明星從東方冉冉生起,明星觸動到他的「本覺」,「無分別心」現前(止觀雙運),體驗「緣起中道實相」,從一切障礙與苦惱中獲得解脫,降服魔軍(克服身魔、心魔、外魔),徹底體悟和親証宇宙人生的真理,見性而大徹大悟(見性成道),證得無上正等正覺,發現原來人人皆可成佛:「大地眾生,皆具如來智慧德相,但因妄想執著,而不能證得。」成為人間佛陀,時年35歲。(菩提樹下悟道 ﹕明星離我那麼遠,何止億萬裡路,光明卻在我眼前,通達無礙。億萬裡路不止,相隔多少光年,這麼遙遠的距離,我都看得到,橫向四方看,也看到無量無邊,我這個見性原來這麼大。見性多大,心就有多大,佛性就有多大,知覺就有多大,所以我這個覺知無可限量。)

釋尊體悟的人生真理與實踐的方法,有別於當時的傳統信仰(婆羅門教)和六師外道,佛陀常說:「人人皆有佛性,眾生皆可成佛。」,這就是佛教的特性。佛陀以深入淺出和入世的教法,來推展他的體悟。 首先在波羅奈的鹿野苑為他的一群老同修 — 五個苦行者,作第一次的說法(初轉法輪),推動了不共世俗的「四諦」法輪,接受五比丘皈依為出家眾,佛法僧三寶倶足,成立佛教。 釋尊一生說法45年,活動於恆河流域一帶,他教導和接引各種階層男女,不分貴賤,一視同仁,打破當時的階級觀念,建立眾生平等,人人皆可經過修行而成佛的宗教社群,創新的宗教風格和溶入生活的修行,使參與者日眾,佛教因而擴大。
釋尊於 80歲時入滅,逝於拘屍羅城外林中沙羅雙樹下,入涅槃前留下的教誨就是要比丘們「以自己作為島嶼,以法作為根據,以法為師,以戒為師」,遺骨(佛舍利)分八份,被當時各國分別建塔供養。
作者:陳家寶醫生
私人執業婦產科專科醫生
於2011年取得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(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)。
在港大修讀時,曾任香港大學學生會佛學會第一屆主席。
資料來源:mind2spirit

管理情緒 更要管理欲望
《法句經》是法救尊者集錄諸經中佛陀所說的偈頌而成的經典,其行文平易簡潔、間雜巧妙譬喻,是佛道入門的指南。

「斷五陰法, 靜思智慧, 不反入淵, 棄猗其明。 抑制情欲, 絕樂無為, 能自拯濟, 使意為慧。」《法句經土‧明哲品》
譯文
五陰法,就是「色受想行識」五蘊法,這五蘊聚集在人的身上,便產生了相應的欲望。法,是萬事萬物的總稱。
斬斷五蘊之苦的假相,靜靜思考尋求智慧,就不會再回到無盡欲望的深淵之中,拋棄對所謂世間依靠的幻想,例如權勢、財產、身體、子女等(其本質也是無常)。
學會管理控制自己的情感欲望,不黏著在世俗意義上的快樂,別再放縱情欲操控我們,如此便能自己拯救自己脫離世俗苦海,智慧亦將放大光明。
圖片及資料來源:上海玉佛禪寺

準提菩薩與千手觀音:多臂法相 如何區分?
為了方便教化和救度不同根基、不同需求的眾生,菩薩會化現不同的形象。準提菩薩和千手觀音,就是觀音菩薩的不同化身。準提菩薩,梵名Cundi,意為「清淨」,是藏傳密教尊崇的佛母,蘊含強大的智慧與淨化的力量。在漢傳佛教中常被供奉的千手千眼觀世音,梵名Sahasrabhuja Sahasranetra Avalokitesvara,是觀音菩薩慈悲願力最極致的顯現。兩尊菩薩同具多臂之相,我們可以如何區分呢?

形象象徵不同
準提菩薩的法相,常見為十八臂三目,每一臂持有不同法器,包括代表斷除無明的寶劍,清淨無染的蓮花,堅固智慧的金剛杵等,是成就修行的工具。三目則可洞察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世。準提菩薩的手印為三股印,常坐於青色孔雀王座上,孔雀能食毒草而不傷,象徵準提菩薩能轉化煩惱為菩提。
千手觀音常立於蓮花寶座之上,現四十二臂法相,中央雙手合十,其餘各手同樣分持蓮花、淨瓶、念珠、日輪、月輪等法器,每隻手掌中都有一慈眼,象徵能用千眼觀照十方世界一切眾生的苦難,並擁有千手和無量無邊的法力救度眾生。

身份特質不同
準提菩薩的本質是佛母、本尊,核心經典《佛說七俱胝佛母準提大明陀羅尼經》中,準提菩薩被尊為「七俱胝佛母」,意為過去無量諸佛皆依其法門成就,可見其法門之殊勝。
千手觀音是觀音菩薩的特殊化現,千手千眼則是其大悲功能的直接體現。根據《大悲心陀羅尼經》,修持大悲咒,遍及一切時、一切處,可解救一切眾生面對的疾病、災難、恐懼等苦難。
修持法門不同
修行者通過持誦「準提神咒」和觀想準提菩薩,可淨化身口意三業,斷除無明煩惱,顯發本具的清淨自性,通過相應融入準提菩薩的智慧境界,證得圓滿菩提。千手觀音的大悲咒法,重心在於持誦「大悲咒」,激發修行者的大悲心,感通菩薩願力,獲得消災免難、滿足善願的利益。其救度相對直接、普遍地回應眾生當下的苦難。
準提菩薩強調般若智慧的開啟與個體修證的成就,千手觀音則彰顯了圓滿無礙的救度功能與廣大的慈悲情懷,智慧是實踐慈悲的根本,而救度眾生則是智慧在世間動人的呈現。無論是尋求自我的內在覺悟,還是渴望救度的悲心撫慰,準提菩薩與千手觀音兩位菩薩,都在以各自無量無邊的願力,為眾生指引了通往解脫的方便法門。
作者:黃婉曼
佛學研究碩士。
電視傳媒人,視佛法為指引人生的哲理。與你一起實踐生活禪,跳出無常煩惱的束縛,學習在娑婆世間活用佛法智慧,發菩提心,修行得樂,共成佛道。